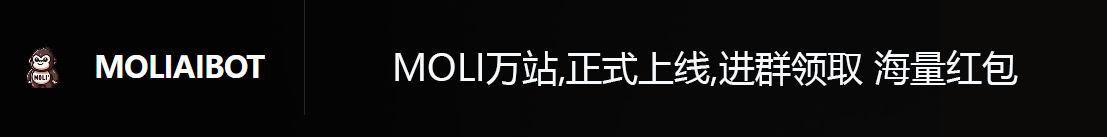FORE Protocol中文网
你的位置:Everyworld中文网 > FORE Protocol中文网 >
南盘江地区早三叠世牙形石生物地层及华南早三叠世牙形石时空演变
发布日期:2025-01-04 11:37 点击次数:174
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发生了显生宙最严重的生物突变事件,导致90%以上的海洋物种以及70%陆地生物科发生灭绝。在这次灭绝事件中,不同生物的灭绝率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古生代类型生物灭绝率远高于其他类型的生物,该现象也进一步导致生态系统结构由古生代类型向中生代以后占据海洋主体的现代类型转变。大灭绝后,极端环境持续,很多类型的生物至中三叠世才复苏,完整生态系统的重建耗时近千万年。然而,研究表明,牙形动物在大灭绝后大约一百万年的Smithian早期就快速复苏。因而,了解牙形石在早三叠世快速演化的原因,对探索危机时期生物的残存和复苏机制有重要作用。牙形石是一类分布广泛,且在早三叠世演化迅速的微体化石,是该时期重要的标准化石,在华南不同的沉积相区都有一定的研究基础。故本文选取华南晚二叠世末期至早三叠世牙形石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灭绝复苏过程。然而,目前华南盆地相区剖面多无完整的Spathian时期的牙形石序列,不能反映该相区早三叠世牙形石复苏的面貌。故本文首先选取位于南盘江盆地内的贵州紫云四大寨剖面和望谟甘河桥剖面进行了详细的牙形石生物地层学研究,以建立完整的盆地相区早三叠世牙形石生物序列。同时,还将位于孤立台地(大贵州滩)斜坡相区的明塘剖面作为盆地与台地之间的过渡相剖面进行了重点研究,以建立两大沉积古地理相区之间的联接。在此基础上,全面收集和整理了来自华南各个沉积古地理相区有较好研究基础的14条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及下三叠统剖面牙形石化石资料,一方面对各剖面的牙形石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和分析(包括鉴定核查和数据统计等),另一方面对各剖面的沉积古地理资料进行分析,确定其当时所处的古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进而探索早三叠世牙形动物的生态分异和复苏演变过程,从而为古生代末大灭绝后,中生代初生物复苏和生态系统重建过程和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也为全面揭示牙形动物这类生态特殊类群在该重大地质突变期的特殊演变历程,提供了新的手段。盆地相区的贵州紫云四大寨剖面,出露有上二叠统(领薅组)至中三叠统下部(新苑组)的地层。经过多次高密度的牙形石采样分析,结果表明该剖面奥伦尼克阶产牙形石丰富,其中包括8个新种,但印度阶含牙形石较为稀少。根据牙形石的产出情况,在本剖面上共识别出10个牙形石带,自下而上分别为Clarkina yini带,Hindeodus parvus带,Neoclarkina discreta带,Neospathodus dieneri带,Novispathodus waageni带,Guangxidella bransoni带,Novispathodus pingdingshanensis带,Icriospathodus collinsoni带,Triassospathodus homeri带,Chiosella timorensis带。在剖面罗楼组下部的灰岩透镜体中产出有牙形石Hindeodus parvus,但在其下的泥岩中产出丰富的三叠纪双壳类Claraia wangi和C.griesbachi等,据此认为该剖面上发现的二叠系-三叠系界线标志牙形石Hindeodus parvus的首现位置应高于三叠系的实际底界位置,故暂将二叠系-三叠系界线置于罗楼组底部。Novispathodus waageni首现于剖面罗楼组顶部(第21层),是该剖面印度阶-奥伦尼克阶界线的标志。其上Smithian-Spathian亚阶界线以Novispathodus pingdingshanensis的首现确定于紫云组中部(第30层)。根据首现于新苑组底部灰岩透镜体中的Chiosella timorensis,可将下-中三叠统界线置于新苑组底部。此外,Scythogondolella milleri在其他地区仅出现于Smithian晚期地层中,而在本剖面上产出于Spathian早期的牙形石Icriospathodus collinsoni带之上,表明该牙形石并未在Smithian晚期的灭绝事件中消失。该剖面的紫云组中还产出丰富的齿台型化石。这些化石的发现表明,齿台型牙形石虽然在中三叠世才广泛分布到低纬度的特提斯洋地区,但是其在Spathian中期就已经在本地区大量出现。说明该牙形石类群在早三叠世后期逐渐发生了生态位转移。另一盆地相剖面是位于贵州望谟的甘河桥剖面,本文重点对该剖面上露头连续的下三叠统印度阶上部至中三叠统安尼阶下部牙形石生物地层序列进行研究。经多次采样和系统的牙形石样品处理,在该剖面上共发现牙形石9属20种。该剖面Dienerian亚期和Smithian亚期牙形石较少,而Spathian时期牙形石较为丰富。根据牙形石分布,可识别6个化石带,自下而上分别为Neospathodus dieneri带,Novispathodus waageni带,Guangxidella bransoni带,Novispathodus pingdingshanensis带,Triassospthodus homeri带和Chiosella timorensis带。根据Novispathodus waageni的首现,可确定剖面印度阶-奥伦尼克阶界线位于罗楼组的下部(第4层)。Novispathodus pingdingshanensis首现于罗楼组上部(第13层)黑色页岩内的灰岩透镜体中,可作为该剖面Smithian-Spathian界线标志。该剖面下-中三叠统界线以Chiosella timorensis首现为标志,可确定于新苑组底部凝灰岩层之上的灰岩层中。贵州罗甸明塘剖面位于孤立台地——“大贵州滩”边缘,剖面出露有上二叠统大隆组至中三叠统坡段组(逐步由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的盆地相演变为中三叠世早期的浅水台地相)。对该剖面多次牙形石样品分析处理,共获得牙形石标本2000余枚,其中较为丰富的牙形石化石产出于Spathian中期。根据牙形石分布,该剖面下三叠统至中三叠统下部共划分出8个牙形石带,自下而上分别为:Hindeodus parvus带,Neoclarkina discreta带,Neospathodus dieneri带,Novispathodus waageni带,Neospathodus triangularis-Triassospathodus homeri带,Chiosella timorensis带,Nicoraella germanica带和Nicoraella kockeli带。但该剖面Hindeodus parvus首现层位之下的罗楼组底部泥岩中未获得牙形石化石,而产出丰富的宏体动物化石,下部以二叠纪类型的腕足类为主,上部产典型三叠纪双壳类Claraia等。据此,该剖面的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应位于该泥质岩地层中部,即剖面罗楼组底部(第4层下部)。该剖面印度阶-奥伦尼克阶界线可根据Novispathodus waageni首现确定于罗楼组中部(剖面第10层上部),该层位也接近碳同位素正向偏移极值。此外,根据Chiosella timorensis首现层位于可将剖面下-中三叠统界线确定于罗楼组顶部。为了探索华南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牙形石灭绝-复苏过程及其生态分异和环境影响因素,本文在对上述3条剖面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还对华南另14条研究基础较好的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及下三叠统剖面的牙形石数据进行了系统收集整理和再研究,并根据其古地理位置的不同进行归类整理,以探索其时空分布和演变规律。根据沉积相特征,将这些地层剖面归纳为4类沉积区,分别为台地内部(包括黄芝山、沿沟、打讲、太平、罐子坝、改毛剖面),上斜坡(包括青岩、明塘、关刀剖面),下斜坡(包括四大寨、煤山、甲戎、边阳剖面)和盆地相(包括平顶山西、作登、甘河桥剖面)。在系统收集前人发表的各剖面牙形石材料(也包括本校各研究组早期对这些剖面研究工作中获得的化石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化石标本和化石图版的系统对比观察和分析,对上述各剖面的牙形石数据进行了全面清理(部分化石进行了修订),共得出晚二叠世末期至早三叠世的牙形石共有28属113种。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华南早三叠世牙形石的分异度、灭绝率、新生率以及不同古地理环境的牙形石生物群的种级分异度进行了分类统计。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在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大灭绝事件中以及之后的Griesbachian早期,牙形动物在各个古地理沉积相区均匀分布;而在其后Griesbachian晚期和Smithian晚期的两次灭绝事件中,牙形动物群向中间水层(即下斜坡)聚集。这两次灭绝事件之间的牙形石分异事件也发生在较深水相区。牙形石的空间分布变化与早三叠世环境的变化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即高温和缺氧的共同作用可能是导致上述早三叠世牙形石的两次灭绝的主要原因;而深水区氧化还原条件发生改变可能促进了两次灭绝事件之间Dienerian晚期至Smithian早期牙形石的重新分异发展。另一方面,牙形石在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大灭绝事件之后均一的分布和形态多样化,可能源自其对灭绝后产生的环境压力的成功快速响应,也体现了其生态适应优势。